记录自然,回归本真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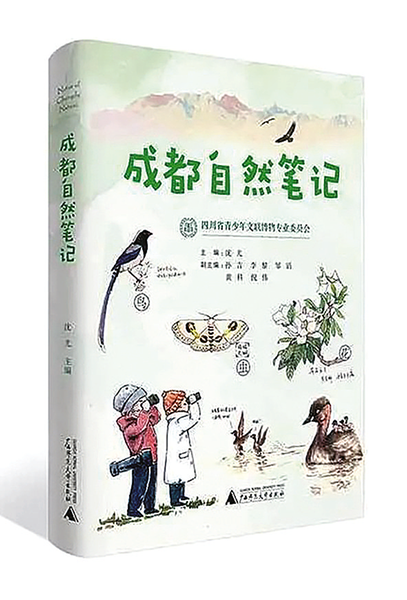
■ 庄平
一年多以前,一册《成都自然笔记》(以下简称《笔记》)在蓉发布,开创了由多名作者就一个城市的花、鸟、虫结集创作的先河。作为其中几个话题的编写者,我自然有几分欣喜。
记得近四年前,四川青少年文联博物专业委员会在成都成立时,《笔记》总顾问之一的刘乾坤先生问我对“博物学”的理解,“玩儿”——我脱口而出。当然,有关博物学的标准答案绝非如此,但纵观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博物学发展,不就是人们在对地理、地质、生物乃至天文等自然现象的不断体验、记录和把玩过程中走过来的吗?甚至,连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东方头号圣人孔子,不也是教读书人闲来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吗?因此,我更倾向于认为,人类亲近自然并不需要多少外力的鞭策,而是出于与生俱来的天性。
我生长于重庆缙云山脚下,那个年代的孩子所读课本的总重量大约不会超过30斤吧,比之当下的孩子们,真是惭愧至极。但那时的我们,却有大把的时间在户外撒野,方圆十里八里都是我们的乐园。钓鱼、扑蝉、抓蟹、摸虾、掏鸟蛋,几乎是个个男孩子必须精通的技艺。至今在我的记忆中,还保留着“地瓜藤”与“鸡眼睛”(裂叶榕别名)淡淡清香与甘甜的味感;对缙云山森林中的“乔巴菌”与野葱的采集与吃法也颇有心得。或许,这也是多年后,我能下决心从事植物学野外工作的原始动因吧。
《笔记》的主编、成都观鸟会创始人沈尤先生,长期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、观鸟推广、自然教育和生态旅游等方面的工作,业内戏称其为“鸟人”。那年,他带着大约十三四岁的儿子同我们一道去雅安荥经县做野外考察。我发现这孩子保持了敏捷好动的天性,并已掌握丰富的鸟类的知识,与当下埋头书斋,面对自然环境通常一脸懵懂的同龄孩子判若两人。原来,他们一家三口每逢假期总有野外安排,观鸟已然成了他们日常的生活方式。《笔记》的副主编之一、博物达人邹滔先生,要么正在贡嘎山拍摄杓兰,要么又在龙泉山观察候鸟迁徙,一年四季总是忙得不亦乐乎。《笔记》的作者之一、孙海先生则告诉我,作为一名文科生他本想鼓励孩子学习植物学未遂,自己却“入坑”成了植物达人,在我手边至少就收集了他编著的《写给孩子们的古典文学植物图鉴》等科普读物3部之多,令我这个一向标榜热衷自然之人也深感吃惊并备受鼓舞。更令人欣慰的是,《笔记》还撷取了一些中小学孩子的作品,呈现了下一代人与众不同的想法。但无论是任何时代的人,你首先应该是个实践者,一个“玩家”。
《笔记》荣获了当年的“坪山自然博物图书奖”10本评委推荐图书。但无论对成都还是世界而言,所收录的28种花草,23种鸟类和20种昆虫,都不过是冰山一角。其可贵之处在于,这个由背景不同的作者所构成的创作群体,成功地将乡土性、知识性和趣味性融为一体,为读者尤其是中小学的孩子们揭开了大自然神秘面纱的一角,从而有助于激发和唤醒人们对自然的热情。
现代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一篇题为《无聊是人类宿命中的定数吗?》的随笔中,有一段十分新奇和令人深思的描述:“我曾见过一个生养在伦敦的两岁男孩,第一次被带到绿色的乡间散步时的样子。时值冬日,一切都是潮湿而泥泞的,在成人眼里没什么让人兴奋的东西,可男孩在这里却表现出了神奇的狂喜。他跪在潮湿的地上,把脸埋进草里,发出含糊不清的欢乐的叫声。他的幸福体验是原始的、单纯的,也是巨大的。他的这种正在被满足的生命需要意义深远,假如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,人很少能成为完善健全的人。”
由此看来,与其说“人们为了生存,聚集于城市;为了生活得更好,而向往自然”,不如说“帝乡非我愿,富贵不可期”,大自然才是所有生命的源头和归属。由此,我以为《笔记》的根本意义和价值在于:引导人们回归自己潜在的“本真”,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我们的终极旨趣。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