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到听见故乡秘密心跳的地方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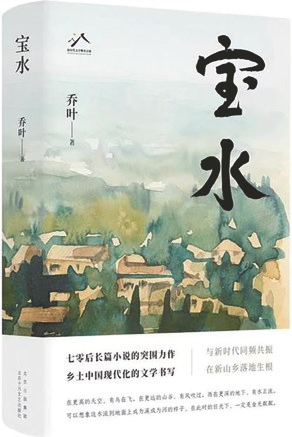
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(2019—2022)《宝水》,是作家乔叶创作的长篇小说。讲述一个村庄从传统型乡村到文旅特色型乡村的转型故事,政府部门、村民、返乡者等多方力量的参与和支持让古老的乡村重焕生机活力。它是乡土中国现代化的文学书写力作,生动地呈现了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的巨变。冬——春,春——夏,夏——秋,秋——冬,四个章节如同一幅长卷,在四时节序中将当下的乡村生活娓娓道来。小说语言朴实自然、平易生动,不事雕琢,平白如水,却有强烈的“土气息、泥滋味”。
题记:故乡精神,老家味道;生活智慧,伦理秩序。
乡愁,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愁?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具象回答的问题。政治家和社会学者关于乡愁的表达,是能够体现各自需要的功能性,但这种乡愁太容易空泛化,难以带来沉浸式的情感体验。
文学的出场,能让乡愁通过无数意象,形成包裹人们精神感知的深广力量。比如邮票,就是一个重要意象。余光中先生的乡愁,就是“那一枚枚小小的邮票”。邮票是薄薄的,小小的,承载的思念却是深厚的,绵长的。乡愁,就从这样的小切口中,弥散出故乡连接世界的深远辽阔。所以,福克纳才这样说:“我一生都在写我那个邮票一样大小的故乡。”
当然,在时代浪潮之下,很多像邮票这样的老物件,已经留在历史记忆之中。乡愁的时代表达,需要找到一个更加完美的意象,来承载地理连接和情感联通的双重功能。作家乔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《宝水》,写的正是这个时代的乡愁。
似乎没有什么比“水”更合适表达乡愁了。水是古典的,也是现代的。万涓成滴,汇流成河,在通向大海的途中,流过的每个地方,都是故乡。水洇于土,土盛着水。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,水的滋养,不只在于肉体与生命,更在精神和情感。上善若水,每个人都需要一汪“宝水”。
《宝水》里的村庄,有一眼泉水,泉眼形状如同元宝,由此得名宝水泉,村庄也因此叫宝水村。这个宝水村,并不是封闭的,也不是逼仄的,而是开放的、宽阔的。从宝水村建构起来的文学世界,表面看来只是一个村庄,但,人来人往,城乡两栖,连接国外,这里也就成了一个村庄里的中国,甚至是一个村庄里的世界。由此,《宝水》寄予的乡愁,有了开放创新的元素。
地青萍,是串起这部小说故事主线的叙事者,也是主角。从某种意义讲,地青萍就是一个寻找乡愁的人。在原本生活的乡村福田庄,以及后来生活的都市,地青萍都找不到“心之安处”。特别是在丈夫离世之后,曾经生活的场景让她眷恋、怨恨、畏惧、逃避,失眠和多梦是她陷入精神危机的表征。为此,青萍需要找到一个可以“睡得着”的地方,来作为自己的精神原乡。
“再造一个故乡”,这就是青萍的选择。从城里移居到宝水村之后,青萍走进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“人情社会”。在这里,她见识了宝水“当家人”大英的泼辣劲儿,也感受了遭受家暴的香梅进行反击的决绝;她看到了返乡靠传统荆编手艺维持生计的大曹的坚韧执着,也了解到很多表面憨厚淳朴的村民隐藏的算计和狡黠,更体会到九奶的隐忍与智慧。在这个“接触-了解-融入”的过程中,青萍重新看见了自己,不仅睡得着,还找到了爱,对福田庄这个原来的故乡有了新的理解——在宝水村,她的乡愁得以安放,她和现实达成和解。
对更多人来说,老家就是永远的故乡,也是精神的原乡。可是城市的二元对立,让无数人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,与故乡形成了隔膜和疏离。和故乡的关系,确实需要重构。但,这种重构的前提,不应该是否定,甚至背叛。这些年,诸如“故乡沦陷”“北上广安不下肉身,故乡安不下灵魂”的表达,多少有些傲慢与偏见。学会倾听故乡的秘密,重新发现故乡的价值深度,更应该是共同的文化选择。
宝水村虽不是青萍的故乡,但二者地理位置离得并不远,人情风俗也很相似,这种恰到好处的距离,无疑为重新思考故乡提供了一个可以冷静旁观的视角。不得不说,这样的设置是很精妙的,在宝水村能“睡得着”,其实是为回福田庄能够找回宁静、取得和解在铺垫。乔叶对待故乡,总是这样充满柔情与悲悯,以向内求索的思维来重构与故乡的关系。
人这一辈子,终会走到向死而生的意识临界点。此后人生,有故乡的人在寻找故乡,没有故乡的人苦楚彷徨。人需要在故乡寻迹到个人精神的始源,找到“到世界去”的精神通途,最终完成一个人“从哪里来”“到哪里去”“回到哪里”的思考闭环。从这个意义讲,我们唯有对故乡保持足够耐心,努力从故乡各种的细节纹理中找到岁月的深度,才能真正找到自我,安放自我。
乔叶的《宝水》能够被认为是一部解开现代人心中“乡愁密码”的著作,正是因为包裹着作者巨大的耐心。乔叶从来不是那种离普通读者很远,却在一夜之间凭借某部作品一鸣惊人的作家。她是一个很早就被人们认识的作者,从故乡低洼的泥泞道路上,一路向着高远处行走,她总是那么安静,那么从容,那么笃定。
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,无数人熟悉乔叶这个名字,是通过《中国青年报》《读者》这类大众报刊。2010年凭借《最慢的是活着》获得鲁迅文学奖,2022年凭借《宝水》获得茅盾文学奖,从文本抒情到叙事逻辑,再到价值深度,乔叶在文学征途上每一步都算数。如此,走出故乡,走向辽阔;回到故乡,回归本源,让无数忠实读者有着共同成长的感动。
找到源头活水,坚持“打深井”,最终完成价值连接,这是文学创作之路,也是生活选择的智慧。从乔叶的创作经历来看,故乡就是她的一汪“宝水”,认识和重构故乡,是她一直在深潜和细挖的事。讲起这本写了七八年的《宝水》,乔叶总是会对那些“跑村”“泡村”的庞杂经历念念不忘,从中不难看出,乔叶围绕《宝水》所做的田野调查是极为细致缜密和详实的。一个好的小说家,并不就是所谓的“大事不虚,小事不拘”,恰恰相反,没有密密匝匝的真实细节,又怎么深谙表达对象的肌理,掌握小说真正的精神内核呢?
耐心决定细节,细节决定品质。迟子建小说关于北纬53°左右的植物和动物的描写,连生物学家们都挑不出错,这就是小说品质底座得以夯实的最好说明。同样,乔叶在《宝水》中对乡村的审视判断,对乡土社会的多维视角和多声部表达,特别是关于村民、乡贤、村镇干部、离乡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梳理,也都是极为准确的,由此也就呈现出一幅极为多元又特别生动的乡村生活图景。尽管一些学院派书评人对《宝水》冠以诸如“乡村振兴文学”“新山乡巨变”之类的主流符号标签,但从根本上讲,《宝水》的创作是完全回到了文学艺术的轨道,完全符合文艺审美的逻辑,而且在价值呈现上,也并没有掉进“伟光正”的传统主流叙事陷阱,甚至还并不缺乏必需的反思批判。
人性、人情、人心,最能真正体现文学的艺术内核。书写故乡的文字,本质上也还是写人。这一点,鲁迅笔下故乡鲁镇的那些人物,如今依然能让读者穿越历史时光,从纸面走进生活,这就是文学的魅力。当然,写故乡的小说很多,赵树理的《李家庄的变迁》、周立波的《山乡巨变》、柳青的《创业史》、莫言的《红高粱》等等,相对于这些旧作,乔叶无疑摆脱了乡村书写的荒凉底色,不再停留在反映愚昧与苦难的层面,而是看到一个更加明媚灿烂的乡村,展示了一群活得很有精神气的乡建者,给如何重构我们与乡村的关系、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参照。正如乔叶直言:“我想写有新特质的乡村。”
乔叶的文字清丽隽永,温婉绵密,极有意味,极具张力。从“美文”作家到小说家,乔叶的语言和思想都在不断迭代进阶,这种文本的价值体现得淋漓尽致,擅用方言,或是悲凉,或是幽默,或是留白,这种极其细腻而又有力的文字,给乔叶的故事叙事增添了太多的美学气质。文字留得住细节,细节养得起思想,思想符合文明趋势,这也是《宝水》成功的重要支撑。
老家很小,故乡很大;故乡很远,原乡在心。很多人未必知道自己从哪里来,但一定得弄明白往哪里去。无论是再造一个故乡,还是重新发现故乡,真正放得下乡愁的地方,一定是在那个闻得着老家味道、听得见故乡心跳的地方。

